郭店楚简中子思著述考中.docx
《郭店楚简中子思著述考中.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郭店楚简中子思著述考中.docx(19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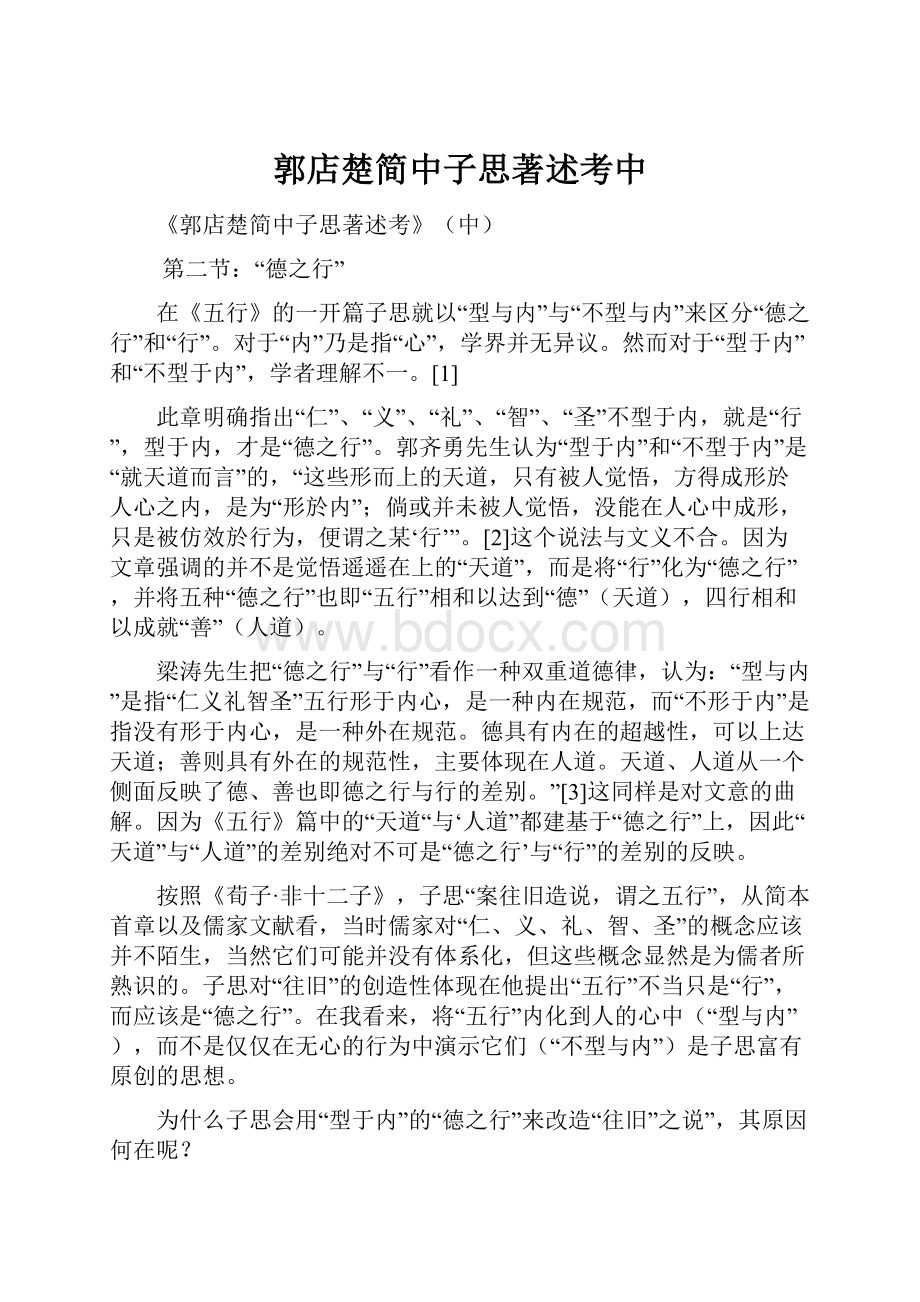
郭店楚简中子思著述考中
《郭店楚简中子思著述考》(中)
第二节:
“德之行”
在《五行》的一开篇子思就以“型与内”与“不型与内”来区分“德之行”和“行”。
对于“内”乃是指“心”,学界并无异议。
然而对于“型于内”和“不型于内”,学者理解不一。
[1]
此章明确指出“仁”、“义”、“礼”、“智”、“圣”不型于内,就是“行”,型于内,才是“德之行”。
郭齐勇先生认为“型于内”和“不型于内”是“就天道而言”的,“这些形而上的天道,只有被人觉悟,方得成形於人心之内,是为“形於内”;倘或并未被人觉悟,没能在人心中成形,只是被仿效於行为,便谓之某‘行’”。
[2]这个说法与文义不合。
因为文章强调的并不是觉悟遥遥在上的“天道”,而是将“行”化为“德之行”,并将五种“德之行”也即“五行”相和以达到“德”(天道),四行相和以成就“善”(人道)。
梁涛先生把“德之行”与“行”看作一种双重道德律,认为:
“型与内”是指“仁义礼智圣”五行形于内心,是一种内在规范,而“不形于内”是指没有形于内心,是一种外在规范。
德具有内在的超越性,可以上达天道;善则具有外在的规范性,主要体现在人道。
天道、人道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德、善也即德之行与行的差别。
”[3]这同样是对文意的曲解。
因为《五行》篇中的“天道“与‘人道”都建基于“德之行”上,因此“天道”与“人道”的差别绝对不可是“德之行’与“行”的差别的反映。
按照《荀子·非十二子》,子思“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从简本首章以及儒家文献看,当时儒家对“仁、义、礼、智、圣”的概念应该并不陌生,当然它们可能并没有体系化,但这些概念显然是为儒者所熟识的。
子思对“往旧”的创造性体现在他提出“五行”不当只是“行”,而应该是“德之行”。
在我看来,将“五行”内化到人的心中(“型与内”),而不是仅仅在无心的行为中演示它们(“不型与内”)是子思富有原创的思想。
为什么子思会用“型于内”的“德之行”来改造“往旧”之说”,其原因何在呢?
在阐明“德之行”的新概念之后,子思提出“德之行五和谓之德”,这两个“德”显然含义不同,“德之行”的“德”是指具体的德目,而后面的“德”是指“天道”,因此笔者试图从“德”字字义演进来对子思提出“德之行”的原因进行一点探寻。
张光直先生指出:
中国古代文明是所谓萨满式的文明,夏商周三代的统治具有强烈的巫术色彩,统治者通过对天地人神沟通手段的独占,垄断与上天和祖先的交通,得以取得政治权威。
而文字符号是沟通天地人神的手段,最初的文字蕴涵了内在的神秘力量。
[4]“古汉字的取象发生与某些巫术仪式‘同形同构’”,[5]作者认为“德”的基本字符“目”就是初民对种子生长发芽的刻画,是一种乞求丰收的巫术[6]。
在“物我混同”的原始思维中祖先被视为族群之种,随着部落酋邦出现,这个向“种子之灵”祈求丰收的巫术顺势演变成了对“祖先之灵”的崇拜,也即祖先崇拜。
商代,甲骨卜辞已是成熟的文字,征之甲骨,可知甲骨文中的“德”仍是对祖先神的祭祀[7]。
《易经》卦爻此辞中出现的四个“德”[8],以及《国语》襄公四年魏降为魏候引周武王时虞人(掌田猎之官)的官箴“芒芒禹迹,画为九州,经启九道,民有寝庙,兽有茂草,各有攸处,德用不扰”都合“祭祀”之义。
殷人的祖先神常宾于上帝神的左右,两者是一元的。
神权与王权统一在一起,“祭祀上帝祖先的权力在商王手中,商王可以按自己的意志和愿望祈求上帝祖先神。
这时上帝天神与民从不来往,也不发生直接关系,上帝与殷人的祖先神仅仅与自己的弟子商王和王室贵族发生联系”[9],通过对祖先的祭祀和占卜殷人在“帝”(天)的护佑下,在“神意”的指导下生活。
当周革殷命,德移鼎迁,周人在“天命靡常”的忧患中反思,“德”的形义在此产生变化,金文在甲骨文的形符上增加了一个表意的“心”符。
尽管金文和《尚书·周书》中出现的大量“德”字都与“行为”相关,但它仍保留“祖先祭祀”之意[10],它更多是表明从周初开始周人重视祖先祭祀中人的行为,西周的礼乐制度就是一整套以祭祀为中心、崇天敬祖的外在行为规范。
因为通过祭祀可以获得“天命”,拥有“德”便有“天命”,必须“以德配天”。
以人的行为而非牛羊牺牲去献媚祖先,以保守天命,开出了一条宗教伦理化可能的道路,而重视“行为”的观念也将导致历史经验(“殷鉴”)成为一个新的维度与天意一起指导规范人的作为。
然而,尽管“敬德保民”是当时政治生活的核心,此时“德”仍是王的专利,[11]天高高在上,神权高于民意。
春秋战国之际,礼崩乐坏,士人崛起,周天子失去了天下共主的权威,丧失了沟通天的特权——“德”,此时“知德者鲜也”(《论语·卫灵公》),在再度的忧患之下,“德”义有了更大的突破,尽管以往的含义仍然蕴涵其中。
儒道解释“德”时多通过“种子”的本喻而展发。
[12]道家在本体论的范畴讨论“德”,将“德”义抽象化、哲学化;而儒家则立足于“德”的社会内涵,承袭西周“德”中的“重行”观念,将“德”行为化、人文化,由“祭祀祖先”而来的孝悌成为“德”义的中心内涵[13],而儒家抽象化的“德”义多与“性”、“命”有关。
儒家对“德”义进行了一系列的发挥再造,并用他们改造的“德”观念去解释并发扬西周礼乐文明,因而形成了儒家文明。
这个过程是由孔子发其韧、子思续其端,孟子推其澜的。
从《论语》中我们可以看到孔子的“德”义因为承上启下而富含新旧解释的弹性,给了其后学各种阐发的自由,孔子之后“儒分为八”自然不可避免。
子思之前,重视人伦日常实践的孔子已经基于“重行”的观念,根据西周礼乐制度总结了各种具体的“德目”来规范社会人伦秩序,如:
“仁、义、礼、智、忠、信”等等,但这些德目停留在行为的层次,是外在的行为规范,被孔门第子实践传习。
笔者以为简本《五行》开篇提出“德之行”与“行”的区别,是子思针对当时“重行”出现的问题有感而发,为了纠正仅仅重行产生的偏差,子思提出了具体的德目必须“型于内”也即“德之行”的观点。
《性自命出》37简说“虽能其事,不能其心,不贵。
求其心有伪也,弗得之矣,人之不能以伪也”;《尊德义》第8-9简说:
“察者出,所以知己。
知己所以知人,知人所以知命,知命而后知道,知道而后知行”,都体现了子思提出“德之行”的原因,子思提出“德之行”目的在于要用具有超越性的“德性伦理”去制衡礼制德目的“外范伦理”。
第三节:
“天道”与“人道”
阐明“德之行”的观念之后,子思在第二章提出:
德之行五和谓之德,四行和谓之善。
善,人道也;德,天道也。
“君子无中心之忧则无中心之智,无中心之智则无中心之悦,无中心之悦则不安,不安则不乐,不乐则无德。
“德之行五和谓之德”,“德,天道也”。
在子思看来,将“仁、义、礼、智、圣”相和谐地“型于内”就是“德”,就是天道了。
天道不是高高在上,不是外在于人的,人通过五行相和就可以与天道合一。
根据今本《中庸》第一节,所谓“和”乃是: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
成型于中心的“五行”必须“发而中节”,可见子思心目中的君子并不是作为一个超越的个体出现的,然而作为一个社会的人,他必须有超越的姿态对人世进行关怀,我们可以在系统规划父子夫妇君臣六位伦理道德秩序的儒简《六德》中看到“人道”成为了“天道”的延伸与体现。
《六德》中多次举“圣”与“仁”其目的正是要融合天道与人道。
“天道”区别于“人道”在于“圣”,“闻而知之,圣也。
闻之而[遂]知其天之道也,圣也。
”(帛书《五行》,第275行),而“智”则是“天道”必须的环节,“君子无中心之忧则无中心之智,无中心之智则无中心之悦,无中心之悦则不安,不安则不乐,不乐则无德”。
“中心”指内在之心,它与“忧”“安”“悦”“乐”这些与“情”相关的词相联使用,可以说是《性自命出》“重情”的发端。
“中心之忧”是达成天道的前提,圣人必须先有忧患意识,然后经由“中心之智”导向“安”、“乐”,有没有内心之乐是有没有“德”的标尺,有德的君子在任何处境都能不改其乐,自得其乐。
正如今本《中庸》第14章1-2节所说: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
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
从人的忧患出发,这再度体现了子思的“天人关系”不是由天到人的,乃是由人到天的,人可以达成天道。
人达到天道必须有志有思,“德弗志不成,智弗思不得”。
志是心的意向,思是心的行为,人与天合一的道路乃在于“心”,于是“心性之说”不可避免会成为紧要的话题,在《性自命出》被专门论及。
尽管子思提出君子通过“慎独”也即保守思的专一便可达成天道,也即“德”,但他的目的显然不是为了宣扬个体内在的超越,正如杜维明先生指出的:
“儒家坚持认为:
终极的自我转化不是超离人性,而是实现人性……一个人只有在社群中才能充分地成为人”[14],然而“一个人要成为充分成为人,就必须同天建立一种恒常的对话关系。
儒家深信,经由自我努力,人性是可以不断完善的”。
[15]在儒者看来君子必须将通过“五行和”而达成的“与天合一”表现在现实的社会人伦秩序之中,“人道”才是儒者最终的关怀。
“四行和谓之善。
善,人道也”,善关乎社会人伦的和谐,所谓“和则同,同则善”,天下大同便是人道的理想。
在人道中“仁”、“智”正如“圣”、“智”之于天道,“见而知之,智也。
知之安之,仁也”(30简),“仁”,《论语》解作“人也”,在《五行》中,“仁”既是人上达天道的起点,又是“礼义所由出也”。
仁之爱,义之行,礼之恭是人道也即“善”的必需,简文第19-21章从与人相交的角度定义何谓“仁”、“义”、“礼”,正与《中庸》第20章4-5节相合:
仁者人也,为大。
义者宜也,为大。
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
人道的实现是“四行之和”,所以同样需要“心”来完成。
简文在论述人道的完成时指出:
“耳目鼻口手足六者,心之役也。
”通过这个役身之心,可以“和则同,同则善”。
《论语·公冶长》记载子贡之言:
“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从整本论语看,孔子并非不谈,只是少谈而已[16],孔子多谈的是人道。
子思的“五行”同样以人道为中心,但显然认为“天道”与“性”不可或缺。
孔子是尊天、敬鬼的,而子思却用“心(性)”将“德”与“行”相联,使得天人可以沟通合一。
人可以通过努力也即五行相合上达“天道”,“天”不再是外在于人、高高在上的存在,君子通过“德之行”达成天道与人道,再用所达之“道”入世,施之于社会人伦,产生了天人关系的互动,儒家外在的伦理道德规范也从此开始被给予了一种内向的超越性,孟子继承了子思的“德之行”的观念,并开出了一个“内圣外王”的方向。
与孟子并称于世的大儒荀子将“礼”作为“人道之极”[17],要求天人相分,提倡礼法,其思想是在“行”的观念下推进的。
因此,子思“德之行”和天人之说只能让他觉得“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并且他认为“五行学说”绝不是对孔子、子游思想的真正理解,思孟误导了“世俗之沟犹瞀儒”,使他们“受而传之,以为仲尼、子游为兹厚于后世。
是则子思、孟轲之罪也。
”孟荀思想的差异体现了儒者在“行”或“德之行”两种观念下的不同选择。
以“德之行”为基础的“五行学说”由子思首倡,这个学说为儒家开辟了“天人关系”、“心性”等崭新而重要的论题。
通过具体的德目内涵于心就可与天人是一,也使得过往外在的儒家伦理具有了一定的宗教性质。
我认为子思思想的重要性在一定程度上可与孔子相比。
因为孔子承袭并发挥西周潜在于“德”义中的“行”观念,用来改造了以祭祀为中心的礼乐文明,标志了宗教伦理化的开端,而子思以“德之行”的观念,提升了儒家的伦理规范,是伦理宗教化的开始,两者无疑都是先秦思想史上的重大革命。
无论“天道”或“人道”都不是“行”的和谐,而是“德之行”的相和,因此都需要通过“人心”。
人所以能够通过“心“与“道”相合,是因为“性自命出”,而人性必须充分体现才可以达“道”,于是“教化之道”就是必须的。
正如今本《中庸》开篇所说: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
儒简《性自命出》从哲学的层面逐一探讨了“(情)性”、“教化”、“心术”,是“五行”学说的可行性基础。
[18]《性自命出》篇与《五行》篇这种明显的相互承接关系是这两篇梯形简同属一书的显证。
对于此点,第二章将会详细论及。
从篇幅来看,《五行》的重点落在了“人道”;从思想来看,《五行》更关心的是“人作为社会人”的实现,儒家一向希望以其“道德伦常”的理念来建立一个“德治”之国,因此人君如何教民,如何为君,社会如何合理地铺张它的人伦秩序,必然会成为探讨的主题。
《成之闻之》讲述君子修身教民的“治国之道”,按首句可定名为“君子之与教”,《尊德义》讲“为君之道”,《六德》讲“人伦之道”,按首句应该命名为《君子求人道》,它们都建基于《五行》与《性自命出》的理论,是“五行学说”必不可少的社会实施方案。
这是本文第三章论述的主要内容。
第二章:
《性自命出》:
“五行学说”的理论基础
第一节.《性自命出》与《性情》
郭店儒简《性自命出》甫一出土即引发了学界研究的热情,因为这是一篇难得一见的重情的古代佚文,并且有助于了解和把握先秦“心性论”的内涵与发展脉络。
已有多位学者对其进行过细致而深入的文本考释,[19],对于此篇的简序编连,学界的认识基本一致,然而在其分篇的问题上出现了两种不同意见。
李学勤先生认为,《性自命出》“从简号一到三六为一篇,中心在于论乐;从简号三七至六七乃另一篇,中心在论性情。
两者思想相关,可能共属一书,然而各为起迄,不是同一篇文字。
”[20]李零先生根据简文标识,将《性自命出》以三五号简为界,分为上下篇,并从两篇思想上的相关性证明六十七支简仍属同一篇文献。
不久上海简问世,其中《性情》一篇与《性自命出》大体相同,其第一章相当于《性自命出》的上篇,而余剩的五章与《性自命出》的下篇大抵相合,只是简序不同。
为深化对《性自命出》文本的理解,陈来先生将郭店楚简《性自命出》与上海楚简《性情论》的文句逐章作了比较,认为郭店简《性自命出》比较完整,而上博简《性情论》则缺损稍多,应以郭店简本为优。
[21]从简文的完整性而言,郭店简自然是更胜一筹,那么两者“何者的章序更合理”,又为何会出现这种章序不同呢?
对此学界略于探讨,因此笔者愿意对此进行一些探讨,以期抛砖引玉。
为了比较的方便,本文采用李零先生的分章。
李零先生用“凡”字为标准将郭店简《性自命出》的分为20章,其说甚是[22]。
根据简文的文意,《性自命出》一文可以细分成四段。
第一段(第一章到第七章,简1-简14的上半部分),探讨的中心是“心性”本体。
第二段(第八章到第十二章,简14的下半部分—简28),围绕“教,所以生德于中”,着重自然人性的“喜、笑、哭、悲、哀”等自然人情来强调诗书礼乐的教化,特别是乐教。
此两段构成了《性自命出》一文的上篇。
第三段(第十三章到第十五章,简36到简49),提出“虽能其事,不能其心,不贵。
”强调在“仁”“义”“忠”“信”等道德之情上要“求心”而不可“伪”。
第四段(第十六章到第二十章)重点在探讨身心关系和修身理论。
此两段构成了《性自命出》一文的下篇。
按照这样的段次,对照上海简,可以发现上海简与郭店简的最大区别乃是将第四段排在了第三段之前,并且第四段的章序与郭店简有些差异,其章序为:
16、20、17、18、19。
比照简本《五行》篇的结构与内容,不难发现《性自命出》与《五行》有遥相呼应的关系。
《性自命出》在第一段提出“性自命出,命由天降”等心性命题,目的在于指出“德之行”可以实现的心性基础。
第二段提出“教,所以生德于中”,也即“天道”——“德”的实现方法。
由于君子有“德”的最终的目的乃是“善”——“人道”,也即“唯人道为可道也”,因此第三段再次强调了“德之行”的必要性,也即“虽能其事,不能其心,不贵”,之后在第四段指出君子如何实现“人道”,也即“修身近至仁”,并具体探讨身心关系,以“君子身以为主心”来呼应并简本《五行》的“身心”学说——“耳目鼻口手足六者,心之役也”。
基于上述的分析,笔者以为《性自命出》的段落较之上海简《性情》更具合理性,上海简《性情》将第四段提前,无疑使文章的内在脉络显得不甚清晰。
那么两者在第四段的简序上到底孰更优胜呢?
先列《性自命出》的第四段的简序:
16.凡人情为可悦也。
苟以其情,虽过不恶。
不以其情,虽难不贵。
50苟有其情,虽未之为,斯人信之矣。
未言而信,有美情者也。
未教51而民恒,性善者也。
未赏而民劝,贪富者也。
〔未刑〕而民畏,有52心畏者也。
贱而民贵之,有德者也。
贫而民聚焉,有道者也。
53独居而乐樂,有内()者也。
恶之而不可非者,达於义者也。
非54之而不可恶者,笃於仁者也。
行之而不过,知道者也。
55闻道反上,上交者也。
道反下,下交者也。
闻道反己,修身者也。
上交近事君,下交得56众近从政,修身近至仁。
同方而57交,以道者也。
不同方而交,以故者也。
同悦而交,以德者也。
不同悅而交,以猷者也。
门内之治,欲其58逸也。
门外之治,欲其制也。
17.凡悦人勿吝也,身必从之,言及则明举之而毋伪。
18.凡交毋烈,必使有末。
19.凡於道路毋思,毋独言独60处,则习父兄之所乐,苟毋大害,少枉入之可也。
已则勿复言也。
61
20.凡忧患之事欲任,乐事欲后。
身欲静而毋羡,虑欲渊而毋伪62,行欲勇而必至,貌欲壮而毋伐,欲柔齐而泊,喜欲智而亡末,乐欲怿而有志,忧欲俭而毋闷,怒欲盈而毋希,进欲逊而毋巧,退欲循而毋轻,欲皆度而毋伪,君子执志必有夫广广之心,出言必有夫柬柬之信。
祭祀之礼必有夫齐齐之敬,66居丧必有夫囗囗之哀。
君子身以为主心。
67
《性情》一篇在此的章序为16、20、17、18、19。
17、18、19、20都在具体谈论身心问题,从文意而言,“君子身以为主心”应该是总结之句,而《性情》篇19章之后与36简“凡学者求其心为难”相连,过渡又十分突兀,因此笔者认为在章序上也是《性自命出》更加合理。
《性情》和《性自命出》段次上的不同,以及章序上的差异,我以为较合理的解释不是《性情》一篇来自不同的传本,而可能是抄手在抄录时发生了一些错误。
《性自命出》一文与简本《五行》篇的内容环环相扣,两篇当同属子思著述,在本章的余下两节,笔者将从“心性论”、“教化心术”角度来阐明它们是“五行学说”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基础,是思想体系的形而上的部分。
第二节.心性论
“德之行”要求人必须用“心”将具体的“德目”内化成“德”(天道)成“善”(人道),但如果人内在缺乏与天可以和一的“性”,那么心思只会枉费,因此心性本体到底如何便成为了能不能贯彻“德之行”的关键。
孟子大力倡导“性善论”提出“仁义礼智非由外铄,乃我固有”来坚固子思首创的“五行学说”,而荀子针锋相对提出“性恶论”来瓦解“德之行”的可行性。
从孟荀“性善”、‘性恶”之争,我们也似乎不难推论出在子思首创的“五行学说”体系中有对“心性”本体的探讨。
那么郭店儒简《性自命出》中的“心性”论是否就是子思的“心性论”呢?
查考简文,其中虽然没有直接标明“性善”,但“性善”论已经呼之欲出。
虽然继承了自然人性也即:
“生之谓性”的传统,但又对道德人性有所发明。
这里的“心性论”具有所有初创理论都必然会有的过渡性和原创性、薄弱性和不成熟性,并且上承孔子下启孟子,是孔孟之间丢失的环节,当属子思“五行”思想体系中的心性论无疑。
简文开篇写道:
凡人虽有性,心亡奠志,待物而后作,待悦而后行,待习而后性1奠。
喜怒哀悲之气,性也。
及其见于外,则物取之也。
性自命出,命2自天降。
道始于情,情生于性。
始者近情,终者近义。
知(情者)能3出之,知义者能内之。
好恶,性也。
所好所恶,物也。
善不(善,性也),4所善所不善,势也。
凡性为主,物取之也。
金石之有声,(弗扣不)5(鸣,人之)虽有性,心弗取不出。
[23]
凡心有志也,无与不(可。
人之不可)6独行,犹口之不可独言也
人人都有性,“性自命出,命自天降”。
既然人的“性”是与“天”相联的,那么人就可能通过这来自天的“性”达到五行相合的“德”(天道)和四行相和的“善”(人道)。
但是这个“性”必须要用“心”去取出,“虽有性,心弗取不出”。
简本《五行》说:
“士有志于君子道为之志士”,只是人心中的“志”没有一定的方向,会随物迁移变化,因此必须通过学习来定志。
同时人天生的‘性”即:
心中的喜怒哀乐之气与好恶表现为外成为“情”,“情”同样会被物所牵引,于是人需要教化来“顺情修性”,以便“生德于中”。
“道始于情”,那么君子需要用礼乐来培“情”,“终者近义”,所以符合“人道”的君主必须“尊德义”,符合“人道’的社会秩序也需要以“仁义”为中心来铺展。
以上是简文前三章阐发的以及必然要引发的内容。
在接下来的第四到第七章较集中地讨论了“性”:
凡心有志也,无(与不可。
人之不可)6独行,犹口之不可独言也。
牛生而长,雁生而伸,其性(使然,人)7而学或使之也。
凡物无不异也者。
刚之梪也,刚取之也。
柔之8约,柔取之也。
四海之内,其性一也。
其用心各异,教使然也。
凡性,9或动之,或逢之,或交之,或厉之,或出之,或羕之,或长之。
凡动10者,物也;逢性者,悦也;交性者,故也;厉性者,义也;出性者,势也;养性11者,习也;长性者,道也。
凡见者之谓物,快于己者之谓悦,物性12之势者之谓势,有为也者之谓故。
义也者,群善之蕝也。
习也性13者,有以习其性也。
道者,群物之道。
从简文一到七章可以归纳出“性”的三个重要命题:
一、“性自命出,命自天降”。
自天命而来的“性”如果不善的话,那么就不会有与天合一的可能性。
然而简文作者并没有明确提出“性善”论,从“善不善,性也”以及“未教而民恒,性善者也”(51-52简)之句,我们又可以看到“性可善可不善”的早期儒家人性观。
二、“道始于情,情生于性”。
《性自命出》最大的特点是以情言性,这是学界的共识。
“情”,也就是“性的流露和发出”,是整篇简文的中心论题。
竹简的上篇主要谈喜、怒、哀、悲、好恶之情,是自然之情,需要礼乐教化以便“生德于中”,可见它“无善无恶”;而竹简的下篇主要谈仁、爱、忠、信之情,属于道德人性论,并突出其在道德实践中的作用,提出“凡人情为可悦也”。
从“凡人情为可悦也”同样可以推导出“性善”的观念。
竹简由上篇到下篇呈现出的这种从自然人性到道德人性的过渡展示了这一“人性”论的过渡性和原创性。
三、“四海之内,其性一也”,“习也,性者”。
这个论题是对孔子“性相近,习相远”[24]的继承与发挥。
正是因为“四海之内,其性一也”所以《成之闻之》提出了君子“欲人之爱己,则先必爱人”的命题,这同样是对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推进。
总上可见《性自命出》一面继承了早期儒家的“性习”论,一面原创了“性善”说,尽管“性善”说并不成熟。
一面继承了“生之谓性”的传统,一面提出了“性自命出,命自天降”的命题。
已有不少学者从“生之谓性”的传统对《性自命出》一文的心性论进行了深入的阐发。
[25]从文字学的角度“生”字是会意字。
取意于草木由地里长出,许慎在《说文解字》卷六说:
“生,进也,象草木生出土上”,多泛指事物的产生与发展。
“生之谓性”这一表示生命与性命的观念最初见于西周周恭王时期的《史墙盘》铭文,其后表示生命之义的“生”在先秦文献中也会写作“性”,马端承在解释《诗经·大雅·绵》中“文王蹶蹶生”一句时指出“生、性古通用”。
到春秋时“生”与“命”开始对举,尽管按照子贡的说法“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但孔子却是常提及“命”的,比如“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五十而知天命”。
笔者认为“性自命出,命自天降”这一人性论的重要命题是子思对孔子晚年一些抽象命题的突破,其中孔子的“天生德于予也”[26]是其较直接的前源。
“德”与“性”是两个可以沟通的概念。
“德”的初形为“种子”,“性”的初形“生”,刻画的是“草木生出土上”,从这里我们也能看到“性”不仅是蕴涵在“德”中禀赋和潜能,更是一种运动,诚如葛瑞汉所指出的,中国古代的“性”不应理解为“出生时的固定本质”,而应理解为“倾向、方向、路径、规范、潜能”等等,[27]因此正